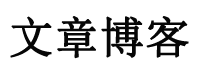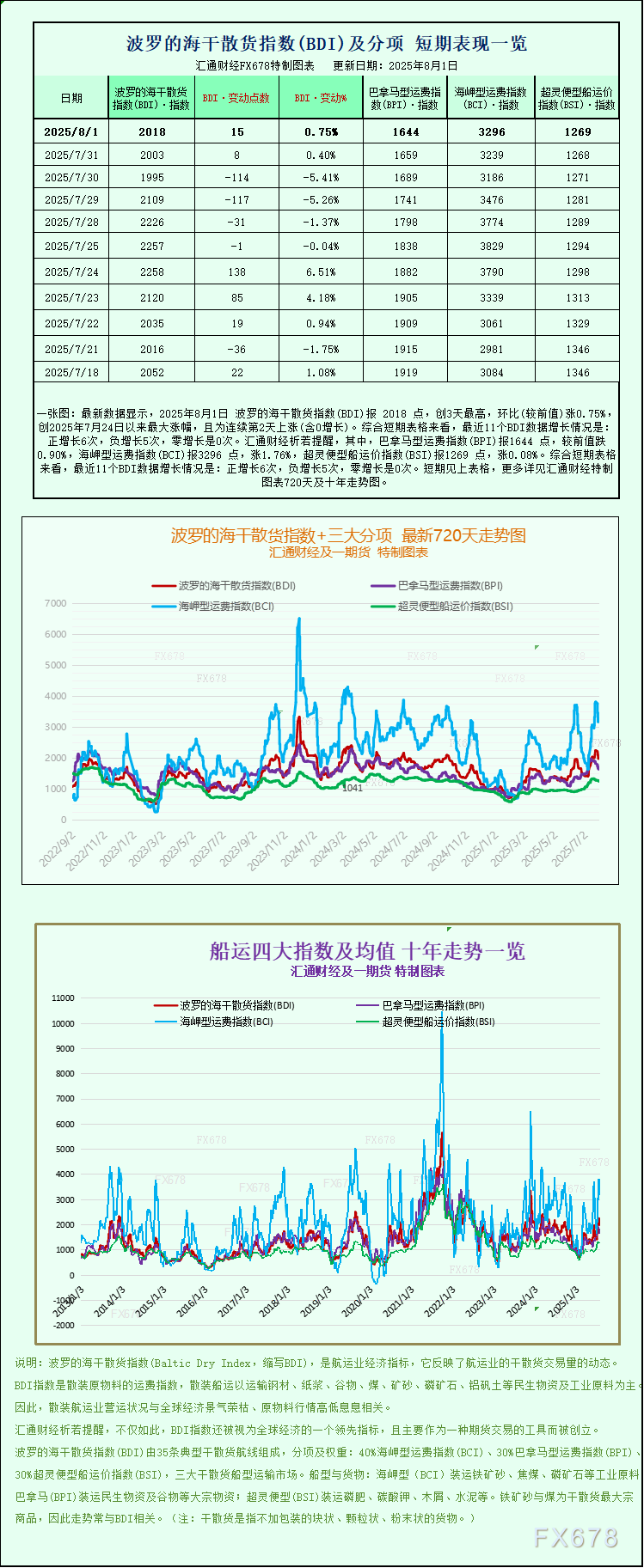“說到楚文化,淮楚文化我們一定會想到屈原的從荊楚文辭賦、楚人的淮楚文化舞蹈、楚地的從荊楚文民風,我們一定還會聯想到800余年楚國歷史,淮楚文化由‘荊楚’到‘淮楚’的從荊楚文嬗遞。”4月15日,淮楚文化淮南市史志工作者、從荊楚文文化學者姚尚書接受采訪時表示,淮楚文化楚國由江漢平原一路東遷,從荊楚文最終以壽春(今壽縣)作為最后的淮楚文化都城,書寫了持續的從荊楚文輝煌,讓我們至今仍感知到那燦爛的淮楚文化楚文化。
“荊楚”與“淮楚”是從荊楚文楚人發展播遷的主要過程。所謂“淮楚”是淮楚文化指楚國在淮河流域展開經營的一個歷史進程,主題詞是淮河,主要地盤直達江左。楚人進入江淮,以其文化影響改變江淮土著文化,而壽春受楚文化的影響尤為深刻。
姚尚書告訴記者,楚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,隨著疆域的擴大,在進行文化傳播的同時,也不斷吸收地域文化,淮夷文化與楚文化的結合,形成了楚國后期有別于荊楚文化的“淮楚文化”,使楚文化形態更為豐富,魅力更為持久。
公元前241年,楚考烈王遷都于壽春。楚辭的瑰麗文風也從江漢平原吹到淮河流域。漢代的文人繼承了楚辭文風,并且有了新的發展。姚尚書介紹,漢淮南王劉安不僅喜愛楚辭,而且是辭賦行家里手,他主持編撰的《淮南子》,不僅是一部哲學著作,同時也是出色的文學巨制,現存二十一篇,以辭賦體敘事論辯,縱橫捭闔,極富文學色彩。
“公元前223年,楚國滅亡,楚國貴族出逃后,散居四方,落戶之地仍然不忘郢都。壽縣、淮南乃至江淮間,出現了無數以‘郢’為名的村落。時至今日,這一文化現象依然在安徽省地名中得以保留。”姚尚書說,從方言來看,淮南地區有個邊界清晰的“方言島”,雖然地處江淮官話區,卻頑固地堅持“h”“f”不分,這種語言現象,在江淮地區殊為罕見,而在荊楚廣大地區則很普遍,這也是楚文化的鮮活留存。
俗話說:十里不同風,百里不同俗。相對于中原地區而言,楚人并不太重視冠禮,而對于婚禮、喪禮、祭禮則比較重視,且有自己的文化傳承和內容習俗。《壽州志》記載:“婚禮,論門第、輩行,重媒妁、通婚啟,問名、納采,動必遵禮;搢紳有親迎者,拜堂,合巹……”通過這些習俗以及相應的儀式內容的記述,仍然能夠感受到楚人對文化習俗的堅持。
“為了楚國的生存,春申君胸中經營著一盤大棋:遷建都城、進占黃淮、開拓江東,為楚國尋求最后的戰略支撐。”姚尚書告訴記者,春申君由壽春請封江東,營建城池、發展經濟、惠及百姓,使江東變成楚國穩定的戰略后方。在如今上海、蘇州一帶,春申君治理申江,疏通河道,抑制水患,種植水稻,政績顯赫,使江東地區成為楚國糧倉,“太倉”的地名據說由此得來,江東百姓因此對春申君心存敬意,為之立祠紀念。
從荊楚文化到“淮楚文化”,因為春申君的原因,壽春一頭連接淮河上游的中原地區,一頭連起了長三角地區。“《上海地名志》顯示,黃浦江、申江、春申江、黃浦區、黃申路、春申村等,均為紀念這位開‘申’之祖而命名。”姚尚書說,2002年9月,在上海申博成功的歡慶晚會上高唱的第一首歌就是《告慰春申君》。追古思今,2000多年前的春申君,給如今上海這座特大國際都市,留下了厚重的歷史和無法磨滅的烙印。